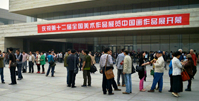- 公告
- 展览
- 讲座
- 笔会
- 拍卖
- 活动
新中国初期浙美中国画教学钩沉
受访者:宋忠元
采访者:葛玉君(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处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方向博士)
一、新中国初期的教学
葛玉君(以下简称葛):宋老师您好,您是浙派人物画“开山五老”之一,对浙派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您也是新中国美术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我想围绕着新中国初期的美术教育等相关问题向您请教。
宋忠元(以下简称宋):好的小葛,谢谢你远道而来对我采访。
葛:我们知道,您是在1949年和袁运甫、方增先等人一起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当时已经把国画科和西画科合并为绘画系了,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绘画系上课的一些情况吗?
宋:新中国初期的绘画系教学比较乱,不能跟现在比了,学生也是变来变去,课只有素描、色彩两门,其他艺术理论主要是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高年级的时候,我印象中也没有上美术史课,经常停课下乡,搞土改,土改就搞了半年,中间搞一些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我们讲是要学四年,49年到53年毕业,但是中间实际上课的时间恐怕只有两年多一点,其他都是搞运动,停课比较多。外语有俄语,当时有一个俄罗斯的人教,解放前可能是学英语。到毕业班的时候上一些白描课,是庞熏琴教的,基本上也是侧重于像西方那种线条。
葛:当时上的线描课、白描课没有提及传统的线描、白描吗?
宋:没有讲传统那样的线条,在四年的学习中间,等于中国画是没有接触的,国画跟油画都并入了绘画系,素描的技法是徐悲鸿从法国带回的那一套。我在一年级时的老师是苏天赐,他当时任助教,是林风眠的高材生。我们一进来有六个班级,日本、法国的教师风格并不一样,倪贻德画的一块一块的,像塞尚,我因为到了苏天赐这个班级,一开始这种影响是林风眠这个路子的,比较古典的;第二学期,到倪贻德教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学的不一样了,说明风格多样的。到毕业班的时候,教我的老师曹思明到北京参加徐悲鸿主持的一个素描培训班,后来回来到我们毕业班的时候,他教的基本上是徐悲鸿这套东西。契斯恰科夫体系则是在我毕业之后引进的。
葛:您的毕业创作是油画《出钢》,当时您主要学习的是油画?
宋:对。因为1953年还没有毕业生,所以从6个班级里面抽出40个学生来组成毕业班,这个班的学生有年纪大的,画得好的,也有家庭困难,希望找点工作抽出来的。大部分基础比较好,毕业创作根据个人的情况都是多样的。像我、方增先、于长弓、全山石四个人画油画,周昌谷是画国画,他以前有一点画国画的基础,他的指导老师金浪让他画《西湖图》。也有画连环画的、画素描的。我画油画,所以我跟全山石两个人到上钢三厂体验生活,我们两个人到工厂里面呆了一个月,在车间里面参加劳动,他后来画了一张《纪念》的毕业创作,我也是画了一张,方增先则画了一张师傅带徒弟的,后来于长弓好像是画了一张冼星海。因为我是在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上素描、色彩课,色彩基本上是油画,不像现在画很多水粉的,我们还是以油画为主,素描也是看哪个老师教了。
葛:也就是说当时的素描风格是多种多样的?
宋:总的来说是徐悲鸿及从法国学回来的那波人所带来的法国的方法,倪贻德的东西喜欢的不大有,苏联的东西还没有进来,大家都是从画册上面看看,像我们个人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像达芬奇、拉斐尔一类的,这跟我们指导老师苏天赐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毕业创作时,也就是生活了一个多月,回来后两个月就完成《出钢》了,时间是比较短的,不像后来一张创作画半年。
葛:我们知道,1952年,绘画系进行油画、彩墨画和版画分科,1953年学校抽掉了您和李震坚等几个人开始进修彩墨画,为彩墨画系师资做准备,您能介绍一下,当时进修彩墨画的一个情况吗?
宋:我们作为研究生,学了不到一年就去敦煌临摹,在去敦煌之前就已经有分工了,我们14个留校的人将来是搞彩墨,还是要搞什么的,已经分好了。也就是彩墨系还没有成立,教师已经分了,专业已经定项了,我们原来是绘画系出身的,定项了油画、国画(彩墨画)、版画。
葛:当时叫“彩墨画”,而不叫“中国画”?
宋:当时的领导对国画,觉得比较封建,可能也要淘汰,所以不用这个名称。我们当时理解可能他们的想法还是以工具来分的。另外,确实当时一些画家的画,包括北京的李斛,他们画的猛一看有点像水彩。我们一进来国画已经没有了,所以彩墨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画,没有去争论说为什么不叫国画。名称跟其他的画种统一,油画、版画、彩墨,一个用墨,一个是用颜色。同时,彩墨画马上就明确了以工笔为主、写生为主、人物为主的教学方针,山水花鸟没有的,有一些临摹花卉。当时的创作要求与普及是有关系的。不提倡临摹很封建的东西,画古装侍女古代的东西……我们1953年毕业,1955年开始有彩墨的,中央美院也都一样。我们就当教师了,当助教,包括周昌谷也是教临摹。邓白、潘韵教人物,山水花鸟这种课是没有的,但是在临摹的时候也临一点,临一点花卉,人物好像没有临摹,临一些技法。
葛:我个人在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个想法,1953年的时候,浙江美术学院成立了民族艺术研究室,潘天寿被安排在这个研究室当中。同样是这一年,在北京文化部批准成立了一个中国绘画研究所,让黄宾虹任所长,王朝闻任副所长。我现在有一个疑惑,是不是在53年的时候,相对来说出现了一点点要重视传统的倾向?
宋:1953年开始重视了。因为我们毕业班(4年级)是开始上课了,老先生还没有启用,潘韵、邓白什么都来上,作为一种国画的技法,也没有讲一定要去学习中国画。因为还是绘画系,这里面有素描、色彩,素描强调用线,主要是为了年、连、宣作准备。素描明暗的东西画年画、画连环画用不到,外国石膏用线来画,你说多难画啊?我们觉得反正你用线画也可以,可以严格地抓形,另外稍微有一点明暗,画得平平的,国外的那种也用线的,但是有一个起伏在里面。林风眠、苏天赐画油画也是用线,不像是后来苏联进来的明暗关系很强烈,画得平平的,很单纯的,很新古典派的系列,所以画石膏是用线,我们也蛮喜欢用线的。
葛:你们毕业时画素描用线,但是这种用线是基于一个画年、连、宣的准备,跟后来讲究的中国画用线是完全不同的?
宋:要求跟国画的用线还是两回事,没有国画老先生的教育。主要是为创作服务。
葛:这个是有人专门指示你们这么画,还是你们自己琢磨用线去画素描?
宋:老师要求的,这个当时主要基于为创作服务,创作为工农兵服务,所以说技法的东西现学先卖,用毛笔勾线也好,石膏像用线来处理,体积用线条来概括,这个不是跟创作结合起来了吗?连环画、年画什么都是勾线的。明暗的东西在创作上用不上去,一般年画上面明暗画得比较弱,这也是符合群众的欣赏习惯,比老区来的简单的用线,要求得深入一点,但是也没有讲关于中国画的那些变化。
二、敦煌临摹、雁荡山写生与永乐宫壁画保护
葛:1954年,由文化部组织的中央美术学院和华东分院的老师去敦煌考察和临摹壁画,可以说是五十年代初期美术界一次较为重要的考察活动,您当时也参加了,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宋:当时可能是要培养师资,中央美院有叶浅予、刘勃舒、詹建俊、汪志杰,他们四个,一个老师三个人,我们这里有7个人,金浪带队的,邓白、李震坚、方增先我这么几个人,李震坚比我们早两届,我们进校的时候他在。
葛:金浪是教什么?
宋:也是画国画的,是从延安老区来的,国画也不是科班的,和曹世明和江丰他们是一块的,比朱金楼早。朱金楼不算是老区来的,他是不是华北师大的我就不清楚了。他主要画水彩,国画没有看他画过,山水自己也画一点,人物跟人家合作,他的造型能力不行,原来不是学素描这种的。用毛笔会用的,年轻老师跟他很熟,我们都说他是教务处长,是领导身份,再加上他又喜欢国画,出去也很重要。邓白是搞工笔花鸟的,人物不擅长,但是以前画过油画,解放前一直在画,属于陶瓷专家,院系调整的时候我们这里工艺系基本上到北京,先到中央美院,然后到工艺美院,专家全部过去,就留了他一个。所以我们恢复国画系的时候,他当系主任,他是工笔国画的,潘老上台当院长以后,他就当系主任,是这样子的。
葛:你们在敦煌主要就是临摹吗?
宋:是啊,我以前等于没有接触过,连毛笔勾线都没有,到敦煌之后,就借一些资料,先给我们一点白描稿,练练笔,练线条,练练手的功夫。我们造型方面强一点,线条功夫临了几天,然后就马上进洞里面去画,因为当时的洞全部开放,不像现在的门要关起来,随便跑来跑去都可以的,没人管。研究所的职能是临摹,他们没有几个人,那时候西安美院也分了几个过去。临摹了将近4个月,也是基本按自己喜欢的,另外有几张重要的做了分工。因为专门有作复制工作的。我们基本上是来学习技法的,也没有专门请人来讲一讲敦煌的风格、技法什么的,我们这里邓白都懂的,我们就是临摹、学习去的。
葛:您刚才说叶浅予也跟你们在一块是吧?他当了很多年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您能介绍一下当时他在临摹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宋:他当时也是在临摹,我们作为一个考察临摹组,詹建俊当组长,大家要集中精力临摹。外面都是戈壁滩,他们感觉有时候来了,汪志杰都想到外面去画速写去,我们不要出去,都得临摹。大家都是很自觉的,觉得很不容易,学校专门派来几个月时间,所以基本上不到外面去写生。大家所以很精心,一般都是自己画自己的,有几张比较大可能两三个人一起画,当时也没有真正的老师指导。敦煌研究所是按照敦煌壁画制作过程来临摹的,我们画画的时候,包括刘勃舒完全凭感觉,表面效果是这样子,我们做写生一样,破烂的东西都把它临出来,感觉很震慑,像墙壁一样,但是人家看起来制作过程不太清楚,敦煌艺术有一些变色没有办法恢复,是复原的还是照它这样子画?照这个现状画,还是半复原?半复原你能够顾及到这个地方是一样的,有的脱落了,有的部分变色了,有的没有变,你按照没变的颜色来画,这里把它恢复过来,感觉新一点,把它完整起来,这个对学习来讲是有好处的。古代制画的程序,先勾线,然后颜色上了以后,再勒出来,底稿是用这个色勾的,最后画的颜色再用勾,可以分析出来的。
现在有一些去临摹就看到表面的,根本搞不清楚怎么样。我们也是抱着一种学习传统工笔画的技法来临摹的,颜色不可能用他们原来的颜色,他们只能用以前矿物质颜色,我们是用水粉色,是买最好的那种进口的水粉颜色。那时候要买大量的石青、石绿不大可能,买了一点朱砂可以直接磨出来,都是很少量的。一般都是要临得很多,面积比较大。材料我们还是用水粉,这种颜色时间长了还在变。敦煌也有好多不变色,青颜色是要变的,白颜色要变的,所以我们看了以后感觉很粗矿什么的,原来没有变色之前也是细线条,所以粗矿的宽线条实际上染出来的,细线勾了以后,边上两条画深一点,中间鼓起来。变成一个宽线条了,所以很粗,尤其画这种飞天,工笔是比较次要的地方画得还比较随意,所以画得很生动。最喜欢这种已经变了色的,风格很粗矿,现在不是不可能这样子,因为唐代以前没有这种风格的,壁画里面保护好的,阳光晒的少的地方,可以看到没有变色跟变色过程。去了敦煌也是学了一些表现方法,了解了一些不同朝代的变化。
葛:《牧区医疗队》是您在临摹壁画回来之后创作的吧?
宋:对。是我们结束以后,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我们这些人分成两个部分,收集素材,参观草原,回到兰州马上创作。周昌谷《两个羊羔》就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他在兰州画了一遍,后来回去又画了一遍。我回来画的是牧区,当地人带到草原里面去访问时所看到的。我们在草地上帐蓬里面住了,因为不安全,有背着枪保护我们的人,也有解放军参加,大概有10来人。有吃的用的,帐蓬都带着去的,医疗队我没有直接看到,但是这种去看望牧民去参访的过程启发了我,就创作了《牧区医疗队》这张作品。方增先在刘勃舒去了天竺后创作了《拾蘑菇》。1955年,周昌谷的《两个羊羔》、方增先的《拾蘑菇》和我的《牧区医疗队》一起参加了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
葛:除了这次敦煌之行,1955年您和潘天寿、诸乐三、潘韵等几位老先生去雁荡山写生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活动。当时是几月份?
宋:大约是六七月份吧,天气比较热,穿的也很少。从敦煌回来以后第二年去写生的时候,好像黄宾虹去世了。1955年在雁荡山住了一个月,因为当时的一些老先生没有被安排上课,学校成立了一个民族遗产研究所,这些老先生在这个里面坐班,朱金楼不是这里的负责人,但是管这个事情,他在教务处也管教育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他组织一些老先生去外面写生,像现在采风一样,我们能画的画速写,老先生他们出去看看,逛逛。说到雁荡山去,老先生蛮兴奋、蛮高兴的。我跟方增先去了,周昌谷大概有课没有去,三个老先生,住在庙里面,另起炉灶的,庙里面吃素的,我们另外一个灶子,吃荤的。
写生这个阶段,我们是想跟着老先生来学习的。照理应该组织我们年轻教师专门听老先生讲讲,但是朱金楼他没有组织,他在外面自己画素描,我跟方增先拿着毛笔带上宣纸去风景写生。没有练过山水,之前也没有练过书法,画出来完全凭西洋画的眼光,我们请老先生看看,老先生也很难受,说像是像的,但不是国画。说你们回去要好好临摹山水、书法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印象很深刻,潘韵先生可以写生的,其他几位老先生逛逛,包括潘老带一个速写本,很小的,勾一点草、石头这样的。他们回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作画,写字,他们聊天,我们也听到一点。我们后来想,他们可能对我们也有所顾及,因为不是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包括领导朱金楼也没有组织给我们讲讲课,我们两个人不好意思来提出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画素描一看根本不像中国画,很难提出问题来。老先生也不好意思来跟我们指导,因为我们也算教师了,年轻教师了,又怕以后承担责任,我现在想很可能是有顾虑的。所以他们当时不大讲,你问问他,他给你讲一讲,我们手头也没有其他画,我们只能是画雁荡山给老先生看一看,他们希望我们多临摹临摹,因为一看我们就是没有一点基础的,如果画过一些山水就好了,可能周昌谷以前临摹过,进校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基础,他教过学生,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当过老师,在这方面技术好一点。我跟方增先两个人都是从画素描开始的,方增先他母亲是画画的,还有一点关系。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到敦煌包括在雁荡山跟老先生开始接触,开始慢慢有影响,我们非常尊重他们。学校领导决定我们画这个,要从事中国画,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有机会碰到老先生,我们请他们指导,老先生也不好说太多,不像后来敢说了。
葛:我看《浙美中国画系65年》册子里有一个年表,这个年表里写着1955年的时候,在楼外楼举行了一个潘天寿60寿辰一个祝寿活动,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宋:我参加了。但是记不大清楚,好像是吃了一顿饭,我们当时属于彩墨画系。
葛:1954年去了一次敦煌,57年带领学生去山西永乐宫是吧?
宋:对。永乐宫那个规模组织蛮大的,中央美院跟浙江美院一道,因为永乐宫要搬迁,整个庙要搬家,怕搬家,先用线把它临下来,保护下来然后再搬。这边是我、邓白、潘韵、金浪、周昌谷。北京去的老师不多,有一个搞壁画的叫“陆鸿年”,他们好像是专业老师,我印象不深,是卢沉他们一届,还有一个姚有多。我们这边是周沧米,作为高年级学生,4年级、5年级的学生,还有刘文西,他们那一届是58年的。高年级的,为学校收集资料的,4年级的学生参加文化部组织的跟中央美院一道,临摹了两个月,时间比较长。我们老师画的是缩小的,对着墙画大轮廓,学习它的造型过程,有一些画得比较复原的,因为还比较新,看得见,不像敦煌已经破了,临摹作为学校的素材。后来给学校同学作为绘画的一些临本。高年级的学生是临原大的。临下来是为了保护文物,因为要搬迁,要造水库了。最后,这个地方也没有淹掉。5年级是为了学校收集素材,现在中国美院藏了这些5年级学生当时留下的这些素材,包括我们临的,在敦煌临摹的东西也都在国画系里。中央美院有刘勃舒,哪一家临的就哪家拿回去,有一些画的永乐宫原大的,可能是文化部组织的,他们拿去了,估计现在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我看后来搬了以后,拼好了以后还蛮好的,蛮完整的,没有什么破烂。
三、彩墨画系——中国画系
葛:1957年,潘天寿出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彩墨画系”也在同年改为“中国画系”,邓白是主任,这个过程或者是历史的背景您能否介绍一下吗?
宋:由于以前取消国画,而且对老先生也没有使用。因此,对中国画当时的领导来讲,至少是抱着那种虚无主义的态度的。一解放,要贯彻新的文艺方针,也是觉得人物画能够表现当代生活,表现今日生活,所以人物为主,彩墨画系的时候人物为主,当时的历史条件是这样子,我们说要埋怨当时的领导,不重视国画,比如江丰、莫朴等人,反成右派也是一个罪名,虚无主义,当然也是认识的问题,不会构成什么反党组织。我们这里莫朴及他的所谓的得力助手,包括对朱金楼、金浪,还有一个金颜,是搞色彩学理论的,美术理论的,即所谓“三金三反”,对国画不重视。如果说不重视呢,成立彩墨系的时候莫朴写文章,实际上已经重视了,但是他们又偏了,为什么山水画会不要呢?人物为主,但是山水画在体制上,在教学上是没有办法上课,当然阐述上要为政治服务,那是一个阶段,所以强调人物画改造,我们拉出来就是作为先培养对象,从西洋画转到国画,从这点上讲,他们已经考虑得比较早了,我们一毕业已经为我们考虑了,要培养到敦煌去了。1957年的时候,批这些领导不重视国画,实际他们首先已经开始重视了,只是在体制上还没有重视。所以一到潘院长的时候,作为一个罪名当然是老先生觉得他们应该把他们的主张提出来,原来是“彩墨画系”,名称当时改成“中国画系”了,这个没有什么争议,我们年轻教师也不参与这个讨论的。潘天寿开始是副院长,后来是院长,他后来提出学术讨论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分科,要书法,这个是很明确的,为了中国画的体制完整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葛:您刚才说到“分科”,应该是1958年提出来的吧,在全国是从62年开始的?
宋: 1957年恢复国画系,58年提出要分科,高年级开始分科,4年级、5年级的学生分科,刘文西他们已经毕业班了,当然不分了,只有两个学生,山水四个,花鸟两个,我爱人(杜曼华)她们是第一届59年毕业的,她就是花鸟系的,还有一个陈照富(音),也是全国专门研究岩画的权威。
葛:我知道在中央美院讨论分科教学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引起了一些争议的,有人是愿意分科,有人不愿意分科,浙江美院当时有没有不同的声音?
宋:浙美倒也没有什么声音,当时总体的影响人物比较吃香一点,大家愿意学人物,很自愿地学山水、花鸟可能也不是很多的,老先生说不管多少,哪怕一个也可以的,那是对的了。人物有8个,他们同班的姚有多的哥哥姚有幸,都是一届的,花鸟只有两个,山水好像四个。相比来说还是人物吃香,所以后来招生都是人物为主,人物比如说招8个、10个,花鸟总是2个、4个、6个,有时候招不到人。分科教学之后基本还是以人物画为主。招生从高年级是58年开始分科,到60年以后到书法成立,完全就分科招生了,老先生也考虑的蛮周到,逐步推下来,开始从4年级,后来从3年级,慢慢从2年级,一步一步宣布,局部变化,大概63年就分科了,这样子招生进来就很少,需要动员。他们第一届的一个书法学生写了一个回忆,书法学的蛮有名的,老先生一定把他拉住了,一定让他学,这个也是从无到有的。
我当时还是蛮赞成分科的,因为有比例在那里了,一个是人物为主,社会需要,当时也考虑工作分配的问题,另外课程在招生量已经有区别了,山水画也少,他们高低班一块上的,4、5年级是一个教室里,哥哥带弟弟一样的,低年级有时候招进来一个跟高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区别对待,老师也可以解决问题,不会说两个学生漏环节,所以说有这个条件分科。
另外课程比例有主科、副科,你学人物画的,以人物为主,山水、花鸟为辅,花鸟画的,以花鸟为主,山水、人物为辅,当时我们的副科比例定好了,这样子出去工作可能方便一点,不会找不到工作,也能画山水画,也能画人物。老先生当是考虑得蛮周到的,一专多能,一个为主科,两个为副科,人数上也是以人物多一点,这样子花鸟少一点,书法更少了,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没有什么。杜老师是分配到花鸟这一块,当时吴茀之是花卉老师。
葛:您是主要教人物这一块?当时负责人物画教学的还有哪些老师?
宋:李震坚、我是最主要的老师了,再老的没有了。李震坚比我大一些,比我们早毕业3年。他们是49年毕业的,我们是53年毕业的,刚解放的时候,李震坚毕业班的时候画的水粉,像油画一样的,他是学国画的,他马上就能够画水粉。解放以后,马上就画水粉画了,所以说他的造型能力还是不错的,他国画书法也有基础。解放前是中国画专业的,毕业以后当助教,我们都把他当老大哥,他刚毕业,所以到敦煌去,他是教师,跟着老先生,我们是研究生,比我大,如果活着的话也快90岁了。
葛:您刚才说的是人物、花鸟,山水这一块谁来教?
宋:分科以后顾坤柏、潘韵。像陆俨少要晚一些,文革之前已经请他来讲课了,人家一般不敢的,我们这里就请他来,因为他右派的帽子还没有撤掉。潘韵也是右派,他们上海帽子摘得慢,外面请来的还是有一点那个的,但是潘老还是敢请的,也就请来了上课,他是很高兴,上海对他没有什么,当时他一个小房间住在我们教学大楼给。当时在浙美像潘韵、陆俨少这样的右派还很多。
四、中国画素描
葛:我在查阅档案的时候,看到1959年有一个关于素描讨论的历史档案,当时是您做的整理,您能回忆一下当时关于中国画素描的讨论的一些情况吗?
宋:哦,呵呵。素描问题讲起来蛮复杂的,这个档案大概差不多。因为提到浙派人物画的问题,既要表现当代生活,又要由中国画来表现。而素描方面一个是中国画用线来造型的,一个是用明暗体面来造型的,这两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人物教师首先碰到这个问题,首先你要教中国画专业的学生,要在素描基础练习的时候,使这种表现方法更适合这个专业,技术课适合专业,如果用西洋画的表现方法,中间要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自己吃这个苦的,我们原来是把西洋画一下子改成中国画,我们从1953年毕业到1954年敦煌临摹弄半年,这样过去,然后在创作中间我们是咬紧牙关,尽量把素描的影子抛开,周昌谷明暗素描画得很好的,而且是这种色彩能力也很强的,都很有研究的,一画就画出《两个羊羔》这种表现方法,方增先你看第一张创作还是有一点稍微明暗的感觉的,我画的也全部单线拼图,像敦煌壁画的这种表现,颜色不是矿物质的,用水粉。就是说也是想避免在表现方法上面,马上用中国传统笔墨上的一种表现方法来融合西方的造型的一种科学方法,我们这样的过渡跟北方有点不一样。
葛:潘天寿主张中国画是以白描和双勾为基础?他并不同意“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基础”,他的这种“白描”和“双勾”和用在人物画创作中的所谓的“结构素描”是否有共同性?
宋:是。他提出来用白描来代替素描的,另外素描可以画一点,明暗不要多,素描不完全排除,速写、慢写,明暗少用一点,以短期作业为主。他提出的这个意见我们是完全接受的。我们当时争论的时候,跟老先生的矛盾是我们年轻教师觉得素描要画的,因为我们自己画过素描,在敦煌的时候,看到詹建俊的速写都画得很好,他说你们到底画过素描没有?你们速写画得好,他是从速写出身的,他靠长期锻炼,包括房子有好多作品,我到他家里面去,那个时候他还在兰州,乡村里面都是速写,他是靠这个熟练以后慢慢摸到造型规律的,我们画素描的科学方法很快能够掌握,现在考学校的不是,短学班的几个月,素描马上就掌握起来了,但是他要速写,要他背,默记,还有一些困难,国画系比所有的系速写能力最强,所以画速写,短期作业画得多,有的时候半天一张,这样子我们出去写生,速写成绩最好。画连环画跟速写能力、默写能力相关,对国画有帮助,所以素描上面改革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潘老有一个观点是东西方拉开山头,大家各自山头,别弄得融合平掉了,特别强调中国画的东西要向中国的笔墨上的要求来发展,西方的东西你可以来吸收,不符合的我宁可不要。所以我们也发现,到83年招研究生的时候,他们提出来作为一个研究生希望素描上再深入画一画,研究生画头像,画得大大的,画的明暗都搞上去,我说你是可以这种试试,不过我估计也没有多大的作用,现在虽还是有一些重新把明暗搞进去,但是跟笔墨还是不好融合,要么你线没有,比如说像毕建勋,他的国画画人物画得很大,你说是中国画?是中国画,但是线出不来的,是素描功夫来的,包括拿出来一批的大画,好多都是这样子,因为要画得深入,画得充分,到后来真正笔墨特点耍的好的没有几个,很多就是要塑造的,靠明暗什么,包括刘文西,我当面跟他提的,头部画得很理性,身上用线条画的,头部要把它体积的明暗,头部画的速写的明暗还是蛮多的,他为了表现体积,不同的形象要表现出来,不得不这样画,身上可以画得概括一点,但是画在一起的时候,好些都不协调。方增先、周昌谷包括我的工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头部跟身体是统一的,包括我们这里现在某一些老师画得也是,画的头部跟身体有区别,也就是说素描上的问题不可能完全很统一了,都觉得要表现人物的时候要表现具体形象,要把它深入,一定要借助这个。
那么中国画讲起来,也可以画的不太像,神态有就可以了,不是很多细节,传神就可以了,潘老他们对人物画要求比较简单,他说你画张飞像张飞,关公像关公,老的像老的,少的像少的就可以了,我们想要个性,这个是有一些细部要画一画,所以素描上这个问题,我们到现在为止,明暗素描还是要画一点,但是不能画多,对这个体积理解以后,不追求过多的层次,所以这个记录上面,当时讨论到的,潘老讲的不要长期作业,搞很多明暗,没有必要,把明暗减弱来这样处理,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素描以线为主,结构出发,只要结构画对了,明暗只是一种辅助,太散了通过明暗把它连接一下,这个东西不是为了明暗而明暗,而是为了更好的表现结构。
葛:以线为主,从结构出发大约是从哪年开始的?
宋:1959年,正式和在教学大纲里面写的很明确的时候是在文革之前,文革后,1983年我到院里工作了,文化部两次国画教学会议都是在我们学校开的,全国的部分院校用我们的大纲,所有的学校都把我们学校的大纲要去,特别是像结构素描,对全国来讲有影响的。方增先是这一派的领军人物,他那篇文章很重要,能够把素描改革的问题解决,我们学校的国画老师包括李震坚都上素描课,都上创作课,不像中央美院,素描课是由油画系老师来上,不是国画老师自己上,所以这个不一样。所谓这派的特点也是在改造融合西方的东西时,从中国画的角度、笔墨要求来融合的,我们感觉开始北京讲国画系,包括徐悲鸿他们的观点是用西方的素描造型技术的基础,用这个东西来改造,用西方的素描来改造中国画,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也融合了,但和我们还是不一样的。
葛:我有一点疑问,您当时学习明暗素描,而为什么在牧区那张画上的表现却是很主观的用线条?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宋:一个是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临摹,敦煌壁画没有明暗,翻翻中国画的画册,中间没有提及明暗什么的,但用线条却很早提出来,包括宋画里面的,包括涵盖人的体积,永乐宫一些造型的形象,一些体积也表现出来了。所以潘老讲的,小孩子画一个圆圈圈没有明暗,人家看起来是圆的,关键是去联想,观察方法跟表现手段与我们当时感觉绝对不一样,西洋画跟中国画的表现,这方面也等于是潘老的一种想法了。
在搞创作的时候,脑子里有一个要求就是尽量把素描,西洋画的因素去掉。一定要坚持用线来塑造对象,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我们看了蒋兆和的画,觉得他的画素描影子蛮重的,用了一点线,但是暗部用毛笔,包括明暗交界线也画出来了,这种表现方法跟线是结合不了的,跟线好象有一个矛盾。刚开始我们参照的是黄胄,中国笔墨还厚一点的,黄胄很生动的,很生活气息的,但线条的速写味道太重了,潘老说像稻草苗,没有笔法,只是生动,所以我们在参照它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线条有一点问题。
另外民间的年画也是单线的,上海画的油墨派我们排除的,这种光溜溜地用明暗,把它平光了,不用线的,跟平光的照片一样,是最早的广告上面用的方法,没有强烈的明暗,没有线。我们觉得要用线,所谓线不足然后再补充一点明暗的效果,所以说在素描问题上面争论了,我们感觉要用中国画来表现对象,如果素描上面不解决,造型问题不解决,我们没有办法教育,所以要改造素描教学方法,当时全国都在推行契斯恰科夫教学方法,我们要改也挺困难的,一方面我们自己来讲素描也不是学得很到家,1953年就这么反反复复,感觉这套素描方法是蛮科学的,苏联的这些塑造体积的一些手段,怎么样把它结合进去,但是在创作上绝对不能露出这个东西来,露出强烈的明暗肯定会妨碍,所以在创作上面在教学上面在逐步改造。
这个里面有一点我们在研究,一方面看了北方的画,李斛他们一派的,我们感觉是写生能力太强,所以我们不能放弃对明暗素描的学习,因为这种方法进步快,又能够理解,所以大学一年级还是明暗画,国画分科以后,白描课也同时进行,也有打架的成分,一方面是明暗,一方面是单线白描,但是这个里面一年级让学生有一个体积的观念,然后到二年级的时候要他去掉明暗,以线为主,结构出发,从对象结构出发,然后明暗辅助,素描到二年级用素描的方法,我们后来所谓结构素描又叫专业素描,国画系特有的。顾生岳退出了学校的素描教研组,他要求到国画系来的,他一来以后,人员增加了,本来是4个人,加上他就5个人,当时一共5个年级,人物画至少一般班有一个教师,顾老师专门对付一年级开门进来的,“明暗素描”转到我们所谓的“结构素描”。
葛:您说顾先生一开始是画明暗素描的吗?
宋:当时他毕业之后分配在素描教学,那时候还没有彩墨画系,学校有一个指导各个系的教研组,素描教学是统一的,彩墨系成立以后,他就要求到国画系,58年以后就正式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是留下来1954年开始到敦煌去了,已经定向是中国画了,顾先生还是在素描教研组,素描教研组到58年正式撤销了,他到国画系了。他一来,素描人物力量加强了,他喜欢搞国画,素描能力也强,我们5个人一起研究素描的改革,观点比较一致的,希望是逐步来过渡,不要操之过急,把明暗素描有了这个基础以后,然后再转成以线为主,这样这个线比较有东西,而不是空洞的,线概括一个体积,明暗对结构理解了,再加上线来塑造这个体积可能更实在一些。另外,一方面也同时看了传统的绘画,山水人物花鸟,发现中国画的贯彻方法是从结构出发的,关于这方面方增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画造型问题的文章。
葛:方增先当时跟你们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宋:是,这个文章我们觉得很好,把这个结构拿去作为一个博士论文最好,他发现贯彻了这个方法,为什么山水有各种方法,石块的结构,树的树枝,山面也是看体积,来到下面的时候也是用浓淡、前后关系、体积关系来看,花鸟画也是一笔下去,浓到淡,根据它的体积,根据它的厚度来,跟对象有关,不是根据光暗来看的,这个我们觉得所谓人物画里面还有染高不染低,这里慢慢化开来或者染开来,就鼓起来了。这个是我们在中国画传统上面就有的一个观察方法,这个观察方法跟西洋画的表现方法怎么融合起来?所以我们在素描里面提出来以线为主,观察方法是结构出发,然后明暗辅助。
葛:我看到很多书里面写到关于从德国来的素描,包括舒传熹留学德国带回来的和刚才您说的结构素描是何关系?
宋:他是从结构出发,因为当时统一都是苏派的素描,版画系也有一些受欢迎的,也有一些不欢迎的,因为它是表现主义的,德国的素描强调结构,人体结构以外还有一种形式结构在里面,我们中国画可以借鉴,形式结构强化了,画的力度也蛮强调的,层次很多的,是强化的,表现主义强化这种表现素描的形式感,这个对我们中国画都有可取的,包括潘老他画的画面,很强调结构,画面的用笔的力度和强度。德国的素描,潘老等我们觉得对中国画有利的,明暗也不是画得很具体的,苏派的明暗太具体,画得逼真没有必要,这个可取的。我们所强调的素描跟它也有一点不一样,形式上的东西,形式结构的这种线条不去强调它,不是一个结构关系,但是为了形式需要加强这个直线,这种形式上的结构还是比较强调的。
葛: 60年代,博巴来浙江美术学院讲学,他好像也是和苏联那种素描不一样,也是强调结构方面,他跟你们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宋:没有直接关系,他的油画表现方法比较表现派一点,表现主义一点,不像苏联的一套。现在有人写文章颠倒了,说博巴是强调结构的,用线来概括对象的,影响了潘老,潘老再影响我们。《美术报》有个编辑写的文章,他搞错了,因为开始来的时候,苏派一统天下,不太吃得开,各个学校的学生终究也是一个风格,所以办到这里,不是很有水平的,教师也不是很有水平的,有一次机会他们能够跟专家学,当然也好的,跟我们强调的素描根本没有关系。博巴很欣赏潘老的画,因为觉得潘老尽管是画花鸟的,但有一种结构,构图上面跟他有相通点,所以他很尊重潘老,为潘老画了一个像,是这么一个关系,现在有些人误会了,颠倒过来了,他实际上向潘老学习的。
葛:1963年之后成立了书法专科课,这个科的成立您觉得对中国画教学在当时有一些什么影响?
宋:这个还是好的,我们专门请来了书法老师,又教文学,又教书法,而且当时规定早上起来第一节课自修课,梅、兰、竹、菊、书法天天练,就像以前读毛主席的书天天读,早上就是梅兰竹菊和书法。书法上了课以后,因为书法时间不能占太多,一个礼拜两节课,然后规定要做作业,你要课外写。60年到65年出来的学生都受过书法训练。文革中断,文革后恢复,现在还是有书法课的。
葛:当时还开了诗词课,好像别的学校一般不是特别重视诗词的。
宋:开古典文学课,另外诗词题跋课,也单独为老师开课。我们有时候晚上,有时候下午,但是不排课,讲好一个礼拜一次,这样的课可以提高大家的修养,提高文学修养,能够看古典的画论比较方便一些。这实质上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课程。不是完全从画面需要上,以前人物画、山水、花鸟做配景什么的,还是为人物服务的,现在单独作为一种艺术,山水花鸟单独一个画科,书法也是一个艺术。诗词题跋这些古典文学也是完全为了提高全面素质……现在诗词题跋课好像没有了,古典文学还有。当时还请了一些外校的老师比如俞剑华、石鲁、叶浅予、盖叫天等人来做一些讲座。有一些等于结合有理论课,有一些是专题讲座,有的是全校参加,有的是国画系的,像盖叫天是全校可以参加的,他的表演艺术,各个系都可以作为艺术的欣赏课,边做边讨论,边表演。叶浅予等这些都是到我们系里来的,到国画系的,反正过路的一些画家,他们好像来玩,到这里来有一个交流,老教授认识的约他来。等于是文艺理论课,专题讲座。
五、浙派人物画的特点
葛:浙派人物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不少相关问题了,但是我想最后还是请您简单地概括一下浙派人物画与徐悲鸿、蒋兆和,包括和叶浅予、黄胄他们这些人的主要的区别,或者您在当时这个大范围之下是怎么来认识浙派现象的?
宋:浙派,我现在看等于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有一些人好像钻到所谓浙派的大旗下面,实际上浙派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浙派已经是区域性的,而不是表现艺术的风格或者是特点。解放初,50年代开始,全国的文艺方针,要表现现实生活。要用传统的东西表现现代的人物,在50年代是很困难的。当时没有什么人,我们只看到黄胄、蒋兆和比我们走得早一点,已经开始画现代人物了,像黄胄也是画新疆毛驴什么的。蒋兆和我们感觉跟我们中国画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们想的是,你提的是,当时大环境下,这个环境是一致的,为了贯彻文艺方针,大家表现当代生活,南方、北方,包括杨之光他们中南的,当时50年代他在中南的,武汉的,还有王盛烈东北的,都是一样的,解放以后都要贯彻文艺方针,表现工农兵,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
为什么所谓浙江跟北方、跟东北、跟南方的岭南派有一点不一样呢?可能跟我们这里的中国美院的一些老先生,潘天寿等这帮老先生,他们参与了对人物画改造的一种思想,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领导要恢复国画,要改造人物画,我们5个年轻教师要担任改造人物画的要求。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办法的,别的路没有好走的,给你搞国画,而且你要画人物,李震坚也要画人物画,花鸟什么的,也是不得不画当代的那个,不能画古代的东西,要画当代的。当代的少数民族也是当代的,新疆的这种容易画,我们作为南方人,表现当代的时候,要画浙江的农村里面的情况。
当时城市里的衣服也是灰溜溜的中山装,男男女女都分得清楚的,所以画人物是很痛苦的,色彩也难画,造型也难画,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是潘老给我们的印象。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课,我们作为年轻教师是1955年开始接触到潘老等老先生的,读书的时候没有接触到国画老师的,我们接触到比较西化的老师,画素描的,到国画的时候接触到潘老,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明确的要求你要用中国画笔墨特点。造型最好是用白描来造型,用线来造型,我们毕业创作的时候,最早的第一张两个羊羔,我们作为国画教师要创作这个,我们说我比他们转的快,其它地方几个人,包括刘勃舒他们,他们北方的包括东北的素描味道蛮重的,南方的杨之光他们水彩味道蛮重的,那我们自以为觉得一开始像国画。西方明暗都去掉了,我们的立场,是跟潘老的影响的非常有关系的。
这个是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尤其潘老在素描座谈会上提出来,素描座谈会时他已经当院长了,主张已经有了。他对我们的作品提出来,你们脸没洗干净,脸没洗干净就是明暗东西太多了。在北京,他们虽然也去敦煌,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受什么大的影响。他们可能是蒋兆和老师影响深点,明暗的东西还是不完全丢掉的,那我们一开始创作就是丢掉的,最先就是在笔墨里面怎么来发掘,能够把形结合进去,这个可能是关键的地方,我们比他转的快。后来到五七年恢复国画系以后明确了,分科,全国最早,我们所谓专业素描就开创开来了,以线为主。到了别的学校他可能也有,但是他没有那么明确的国画素描,东北他们素描画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素描味道重一点,其它就是一个总的气候是一样的。另外呢,潘老他们老一辈的印象再加上我们转的快,跟人家不一样,因为我们做了比较,我们看了蒋兆和他们画的,看看是好的,可是跟潘老要求的不一样,不是用线,是用别的。
所以我们尽量避开这东西,尽量在笔墨上面多学点,我们到永乐宫临摹也蛮积极的,后来到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馆,我们都是几个老师去里面的,到故宫博物馆我都去了,到上海博物馆展馆里面临摹的,条件不好着呢!我们尽可能听老先生意见,传统的笔墨重视一点,在教育学生中也要强调这一点,逼迫自己在备课中也要明确造型,要求单线要怪一点,传统的形式感强一点,另外各方面要求全面发展一点。
- >>相关新闻
- • 民国女画家陆小曼: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 • 万鼎携17米巨幅山水画大秦岭走进大会堂
- • 齐白石笔下最漂亮的虫子
- • “苍劲风华——尹默中国画作品展”亮相北京
- • 《松风婧待》李晓松、鲁婧中国画作品展在京举办
- • 中国传统绘画植物的隐喻——草木有情
- • 画家闫勇:写意不可“贫学” 先论功夫再谈格调
- • 画家许翰政:从画者的角度思考绘画
- • 天津美院中国画都创作基地在潍坊揭牌
- • 天津文化旅游周暨东方艺术展在东京开幕
- • 圣地·后素—姚景卿姚铸国画精品展寿光举行
- • 中国画要敢于面对重大现实问题
- • 钟章法:当下中国画缺少精神内涵
- • 云海画院揭牌仪式暨首届作品展中国国家画院开幕
- • “周京新画展”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 • 第三届大学生(广州)艺术博览会将于12月开幕
- • 知名画家李津国画雕塑作品香港展售
- • 中国画的魅力在于笔墨
- • 画家郑连群巨幅国画将亮相天津机场新航站楼
- • 发现大师系列:张采芹艺术作品鉴赏

- • “画说天津”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研讨会
- • 苍劲恬然凝重朴实—李克玉书画作品评析
- • 水墨计(肆)十二人展将启幕 天津美院薛明入展
- • 王书平:与潘基文谈画的“东方鹰王”
- • 《光环的背后:我与名人》首发签售会11月2日举行
- • 百年书香 艺术精品——《华世奎书法作品集》出版
- • 天津文化旅游周暨东方艺术展在东京开幕
- • 圣地·后素—姚景卿姚铸国画精品展寿光举行
- • 书画家梁旭华的艺术世界:以字入门缘定山水
- • 挖掘传统 借古开今—薛永年谈李毅峰的山水画艺术
- • “荷语—郝跃先个人作品展”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开展
- • 韩必省书画作品展暨慈善捐赠活动在北京举行
- • 天津美院教授著名画家何延喆80年代山水画课徒稿
- • 天津艺术家张羽:毛笔皴擦掉了当代水墨精神

-
 赵国经、王美芳
¥ 0
赵国经、王美芳
¥ 0
-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王学仲:《垂杨饮马》
¥ 0
-
 何家英:《醉艳》
¥ 0
何家英:《醉艳》
¥ 0
-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
萧朗:难忘十月醉金秋
¥ 0